诗不可说丨诗路车辙,中华古典诗词中的车马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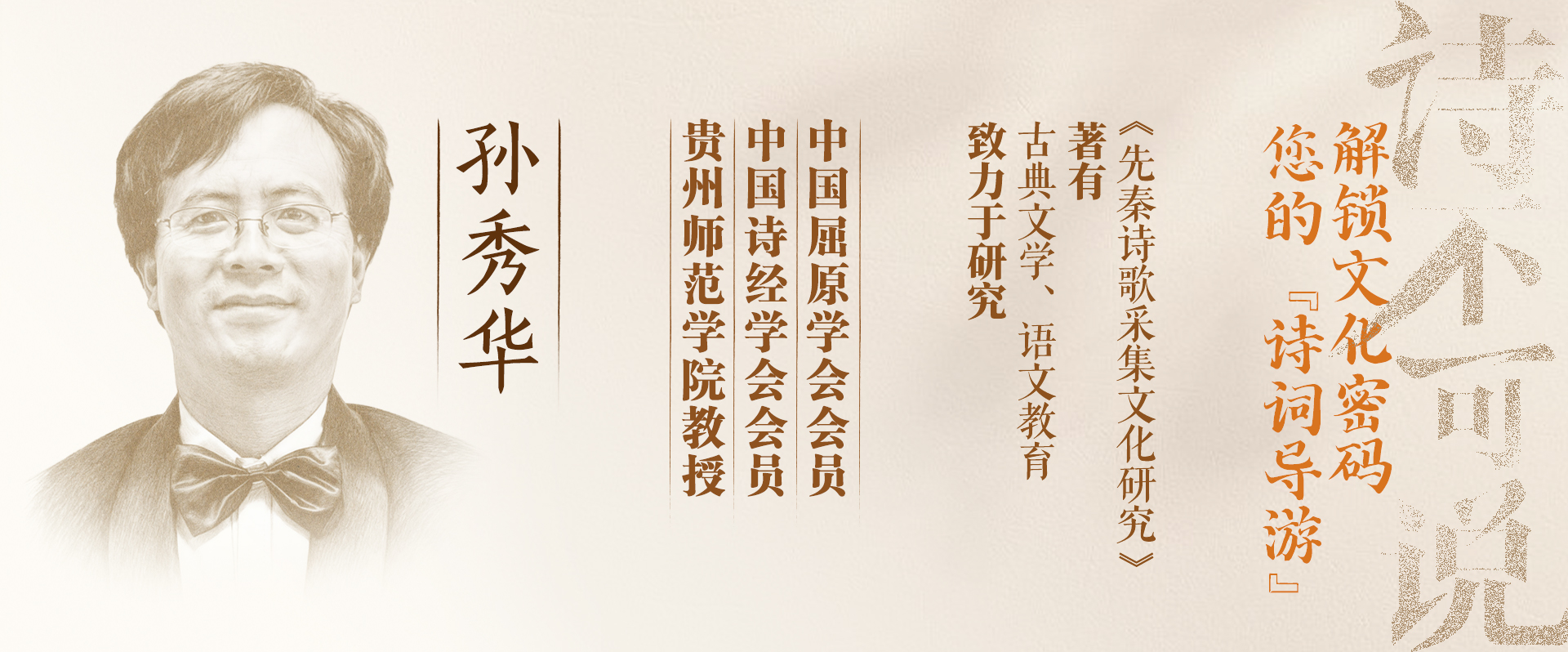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诗圣杜甫《兵车行》开头的感叹如此沉痛。“征人遥遥出古城,双轮齐动驷马鸣。”中唐张籍在《杂曲歌辞·车遥遥》中如此描写描绘征夫出征的场景。这样的车马滚滚,扬起的不仅是烟尘,更是千年的诗情。古道西风,驷马嘶鸣,每一道深深的车辙里,都藏着古人说不尽的悲欢离合与家国情怀。车马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礼制规范、社会地位、家国情怀和细腻情思的文化符号。从《诗经》中的“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到唐诗宋词里的“宝马雕车香满路”,车马这一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从未缺席。

开篇便是华章,最早最集中的车马歌吟来自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据统计,《诗经》中直接提及马与车的诗篇有六十余首,占总篇数的五分之一强,车与马已成为构建周代贵族生活图景不可或缺的绚烂要素。这些车马意象,首要承载的便是森严的礼制内涵。
如,《小雅·采芑》把周宣王卿士“方叔元老”帅大军出征的军容夸饰赞美为“其车三千”,且重章叠句三言之。又描述诗云:“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以及“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还有“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这简直就是“盛大阅兵直播”啊,战车三千辆,战车三千辆,战车三千辆!帅车车辕饰以朱漆,车衡上绘有花纹,马匹佩带的八个鸾铃响声清越。凯旋献俘,战车行进,轰轰隆隆,如雷如霆!而其实,车饰的差异,直接标志着主人爵位的高低与场合的尊卑,这首诗里的车马描绘,又并非单纯的文学描写,而是严格遵循《周礼·春官》中“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五等车制的礼制体现。
又,《召南·何彼襛矣》有曰:“曷不肃雍,王姬之车。”这是写周天子的女儿下嫁诸侯的诗句。大意是说,“王姬”出嫁的车马,庄重雍容,整齐和谐,符合礼仪规范,和和顺顺。《诗序》注解云:“《何彼襛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换另个一视角,写诸侯娶妻场景,赞美周天子女儿的豪华出嫁车队,《大雅·韩奕》四章有曰:
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韩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
诸娣从之,祁祁如云。
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其中“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三句夸赞新娘子车队说,百辆车队送亲,声势浩大;驷马八鸾,串串銮铃锵锵作响;王姬出嫁的车队非常显耀荣光。

车马离不开道路,从《诗经》看,周代“中央政权”修建管理运行的“马路”——“周道”,是确定无疑存在的。“周道”作为一个词语在《诗经》的四首诗里出现五次,“周行”在《诗经》的三首诗里出现三次。另外,在《左传·襄公五年》中还有逸诗“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有些诗例很写实地指向道路“周道”,如,《小雅·何草不黄》四章诗曰: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后两句是说,高高的役车,驰行在大路上。
在这样的“马路”上驱车奔走,“道义”是具体的,忧君忧国忧民,“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小雅·大东》首章歌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其忧心忡忡,甚可怀也!又如,《鄘风·载驰》首章诗云: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小雅·北山》诗曰:“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诗经》中的“王”均指周王周天子,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语即出自本诗。确实,天子管理的天下事无休无止,以致于在《诗经》里“王事靡盬”的说法居然成了“流行语”,分别出现在五首里,且出现次数达十一次之多。而《小雅·北山》这首诗还有“四牡彭彭,王事傍傍”的“变体”诗句,这“彭彭”“傍傍”押韵,说法不同了,但意思还是驱车在途,疲于奔命,操劳“王事”,无休无止。
尽管“无国要孟子,有人毁仲尼”,然而,“朝闻道,夕死可矣!”“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的“载驰载驱”,心怀天下,在孔子、孟子周游列国的生命追求中书写了成光照千古的辉煌史诗。
对于给两个儿子取名苏轼、苏辙,苏洵写有小文《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文章大致意思是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都各有职能,而唯独车轼好像是没有用处的。虽然这样,如果去掉车轼,那么我们看见的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轼啊,我担心的是你不会掩饰自己的内心。天下之车,都遵从车辙上碾过,而谈到车子的功劳,车辙却又从来是无功的。虽然这样,遇到车翻马死的灾难,祸患也从来波及不到车辙。这车辙啊,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的。辙啊,我知道你是可以免于灾祸的。
而从老爸苏洵的内心探求,最值得推崇的以马车的部件命名的堪为两个儿子终身典范的古仁人贤圣是谁呢?必然是孟子!
孟子当然不叫“孟子”,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轲”的本义为接轴车;“舆”指车厢,引申指车;孟子的“名字”是完全与车马相关的。后人把孔子孔丘和孟子孟轲并称为“丘轲”。唐代韩愈《石鼓歌》有曰:“方今太平无事日,柄任儒术崇丘轲。”所以,人到中年发奋读书的“有为好大叔”苏洵,从马车部件上给两个好儿子命名,或自有其潜在的一心慕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远志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最终,父子三苏,风华绝代,千古风流。
近世,最具影响力和积极意义的关乎道义与家国情怀的“车马”事件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指1895年康有为领导的一次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举人上书皇帝的请愿运动,因上书的签字者均为各省举子,“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史称“公车上书”。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力主拒绝和议,提出四项解决途径: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变法建议,实行“君民共主”。并指出前三项只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之本。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开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
中国人对车马的热爱刻到了骨子里,自行车,老人们管它叫“洋马儿”;摩托车,叫“铁马儿”;电动车嘛,叫做“电马儿”。但四轮汽车总归不叫“马车”了,不过即便到现在,无论国道省道县乡道路,都还可以叫做“马路”。
梳理总结,在源头《诗经》中,车马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社会功能的物化,意象庄重、典雅。汉魏至唐,在乐府诗和唐诗中,《车马行》《车遥遥》《兵车行》《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等形成了流行传播,车马成为征戍、行役、离别等人生重大苦痛的标配载体。诗词中的车马,早已超越了其器物本身,沉淀为一种底蕴深厚的文化心理符号,成为一种强大的抒情“套语”和“架构”,就像一组精密的文学芯片,储存着中华民族集体的记忆与情感模式。诗人只需启用“车马”“征轮”“归鞍”等词汇,便能瞬间唤起一整套关于礼制、文化、道义、家国、离别、行役的复杂情感与意境。
当所有朱轮锈蚀、驷马成尘,唯有诗人截取的那个瞬间——车轮启动的轰鸣、长亭折柳的寂静、旧辙平芜的苍凉——在文字中获得了永恒。故而,当我们在诗词中与那些原本渐行渐远的车马重逢,我们触碰的不仅是文学的美,更是先民们在广袤时空中探索、挣扎、思念与回归的心灵轨迹,“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