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唐诗中的芦花与荻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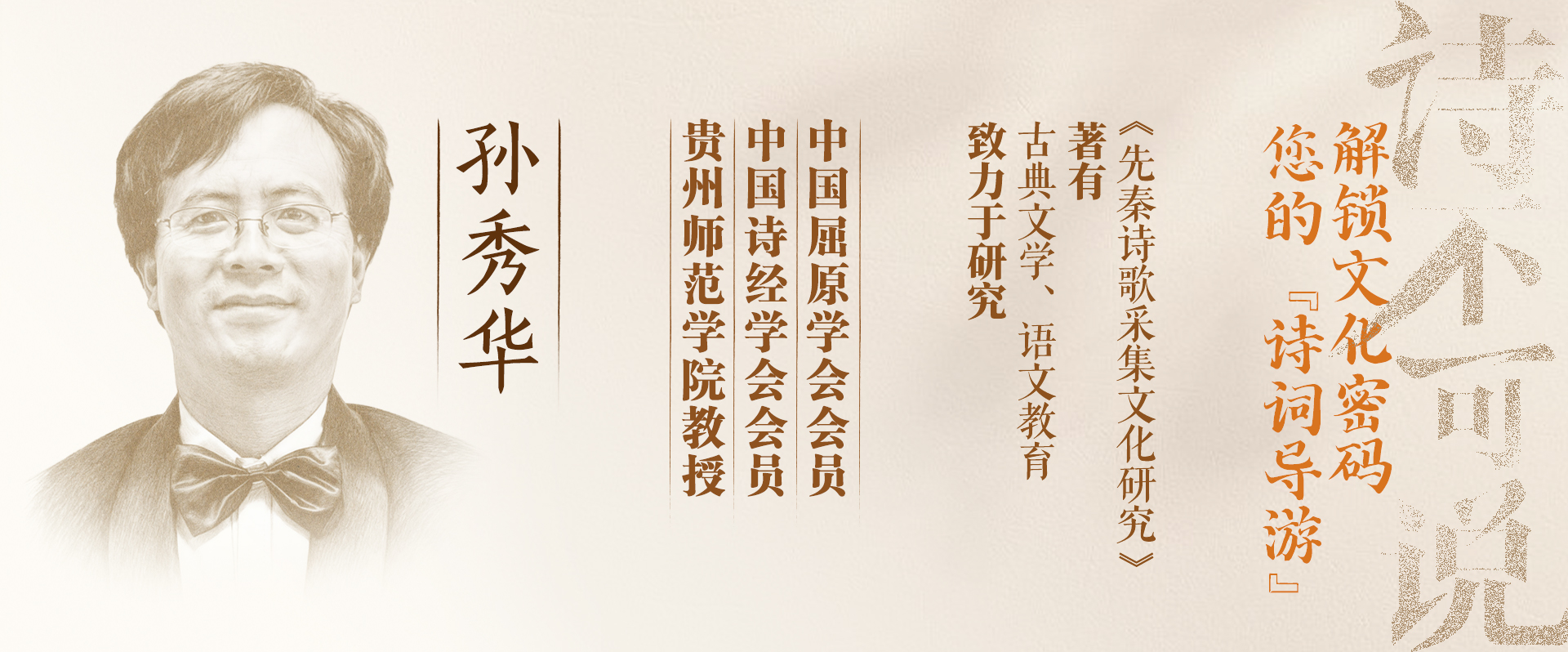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平湖水落苍黄处,一段风烟芦荻花。”“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秋色深,天转凉,如雪的芦花、荻花摇摇曳曳,波浪般起伏,连带着碧水白云,将目光引向天际,让秋色静穆玄远,成了让人触目惊心一瞥难忘的时令风景。

唐诗写芦荻花,主要集中在两个场景里。一是自述口吻,第一视角,江头送别,芦荻花是诗人眼中风景,衬托描画心中别情离愁;二是他者立场,理想桃源,看那江畔渔家自由自在潇潇洒洒,芦荻花是生动点画,抒发着怀才不遇的惆怅与归隐情怀的高雅。

“客路向南何处是,芦花千里雪漫漫。”赠别惆怅,江头湖畔的芦荻花自是“别”样的风景。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诗曰:
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
洲势逶迤绕碧流,鸳鸯鸂鶒满滩头。
滩头日落沙碛长,金沙熠熠动飙光。
舟人牵锦缆,浣女结罗裳。
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全诗都精彩,但最精彩的还是结语。“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如此三句,古意优雅,“风味深永,可歌可言”,“全似《浣溪纱》风调也。”
“西望白鹭洲,芦花似朝霜。”李白写“送别”,也有“芦花”佳句。李白《送别》诗云:
寻阳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里。
胜境由来人共传,君到南中自称美。
送君别有八月秋,飒飒芦花复益愁。
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有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的这首诗《送别》诗则说,“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画面场景类似,二者情味也是一致的,都是浓情化不开,深情恰如江水流,奔涌不止,滔滔不绝。而李白《送别》诗里的“飒飒芦花”,既标明了“八月秋”的分别月令,又突出了离别之愁绪,愁上加愁,“复益愁”。

岑参《楚夕旅泊古兴》有曰:“独鹤唳江月,孤帆凌楚云。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许浑《送客江行》诗有云:“萧萧芦荻花,郢客独辞家。”朱长文《吴兴送梁补阙归朝,赋得荻花》诗曰:
柳家汀洲孟冬月,云寒水清荻花发。
一枝持赠朝天人,愿比蓬莱殿前雪。
“朝天人”是指将要朝见天子的朋友“梁补阙”。诗写送别归京友人,居然想到要折一枝堪比“蓬莱殿前雪”的洁白荻花相赠,如此洒脱俊逸,风流倜傥不减“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自当也是情意深长,雅爱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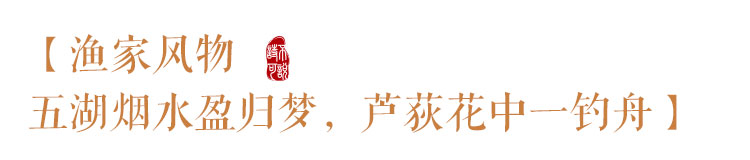
“悠悠兰棹晚,渺渺荻花秋。”古代文士,历经了仕途险恶、江湖风波,往往怀有归梦园田、渔樵山野的念头。即便实际上情况复杂不能真的隐居,吟哦月下,形诸笔端,把“归梦”活画,也常常在友朋间引发广泛共鸣。
韦应物《答李浣三首·其二》诗云:
马卿犹有壁,渔父自无家。
想子今何处,扁舟隐荻花。
“马卿”指西汉绝世大才子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故有“马卿”之称。诗篇愤世嫉俗,韦应物借司马相如有怀璧之才而难得知遇难以施展才华抱负的故事,称赞渔父、扁舟、荻花的生活向往。
白居易《赠江客》诗曰:
江柳影寒新雨地,塞鸿声急欲霜天。
愁君独向沙头宿,水绕芦花月满船。

诗句明白简单如平常话语,“水绕芦花月满船”的画面清晰如在眼前。而这忧愁,却又不仅仅“愁君”,也是白居易自己的忧愁。《唐诗笺注》便体会到:“‘愁君’句不止说江客,连自己亦在内。”与白居易这首《赠江客》诗表达一致,但更显宁静平和,杜荀鹤《溪岸秋思》诗曰:
桑柘穷头三四家,挂罾垂钓是生涯。
秋风忽起溪滩白,零落岸边芦荻花。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有首《芦花动》,诗句紧紧围绕题目发挥,描绘芦花随风翻卷的动态景象,点出游子思乡主题,质朴自然,音韵生动。耿湋《芦花动》歌曰:
连素穗,翻秋气,细节疏茎任长吹。
共作月中声,孤舟发乡思。
耿湋《芦花动》白描如画,声情并茂。推测这首歌诗应该是入乐的,当时可按律歌唱,从而这“《芦花动》”或原本具有“词牌”创制的意味。
雍裕之《芦花》诗云:
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
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
这是一首对于“芦花”的“专题”咏物诗,却也把意象归结为寄予着美好向往与想象的唯美“渔家”。而大家最为熟知的唐代“芦花诗”,应该就是这首司空曙的《江村即事》: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兴趣可嘉”,“不言乐,其乐无穷矣。”《唐人绝句精华》称赞说:“此渔家乐也。诗语得自在之趣。”诗写江村眼前情事,真切恬美,宁静悠然,真率自在,清新俊逸。而如此天真自由的文字,必定出自坦荡无邪、开阔本真的心胸,激荡着澄净的无拘无束的生命去追寻那人生的终极意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芦、苇、荻等等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入诗入歌。在唐诗中,芦花与荻花常常与秋日、离别、隐逸等主题相连,成为诗人表达特定情感与思想的重要媒介。从自然属性来看,芦花与荻花颜色偏白或淡黄,形态轻盈,在秋冬季更为明显入目,这便使它们自然而然地与秋日的萧瑟、生命的无常等情愫联系起来。芦花与荻花多生长于水边,与渔舟、茅舍相伴,这又使它们与隐逸生活、田园趣味相关联。唐代文人多有漫游、宦游的经历,他们常常面对离别与思乡之情,秋日的芦花与荻花很自然地成为他们抒发情感的载体。同时,唐代文人普遍具有隐逸的倾向,当他们仕途受挫或对世俗生活感到厌倦时,往往会向往田园生活,芦花与荻花又会成为隐逸生活的象征。
当然,从现代生物分类学上讲,芦与荻不同属,芦苇是禾本目禾本科芦苇属植物,荻是禾本目禾本科荻属植物。从传统“名物学”视角考察,则古籍中的“蒹葭”“蒹苇”“萑苇”“芦荻”等等如何与现代生物分类学上的“目”“科”“属”“种”一一对应,也是很难厘清的。而据资料表明,仅芦苇属就已有127个种及亚种、变种被命名。已经被鉴定的芦苇品种如,黄芦、白苇、线芦、白毛苇、白皮苇、白穗苇、白花苇、紫杆苇、紫穗苇、紫花苇、大头芦、观音芦、凤凰苇等等。然而,在唐人眼里,芦荻并称、合称都无不可,即使形态有别,却仍情致相通。
“八月九月芦花飞”,“芦花浅淡处,江月奈人何?”“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闲暇漫步,细读唐诗,当我们遇见秋日芦荻,刹那间,节序、自然、历史、现实、文采、情感、欢乐、哀愁、虚无、坚实……都扑面而来,仿佛“似曾相识”,仿佛还能听见那从唐朝传来的芦荻歌诗的清雅回响,那是诗与自然最为和谐的共鸣。


